农场人的下酒菜
石河子日报
作者:
新闻 时间:2024年03月07日 来源:石河子日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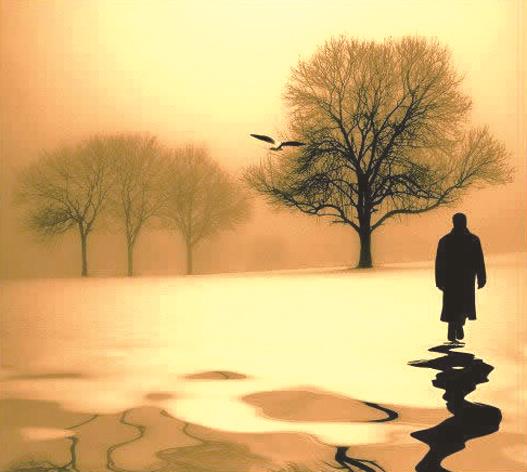
见 证
亲历岁月
■高永明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农七师下野地五场(今133团)开荒队的许多职工都知识,1964年退伍后从四川巴中转业到开荒队工作的鲁山仁,是连队职工中喝酒最不讲究下酒菜质量的人。他一捧花生、一根大葱、一块咸菜疙瘩都能下酒。老鲁的老婆说:“俺家里那个人喝酒最好伺候,下班回来吃饭时,随便有点啥就着就行,只要有酒,滋溜一口,“咕咚”一声下肚,往嘴里塞点啥就完了。”
确实,那年月,农场职工干活回来,吃饭时能巴巴实实喝上几杯酒,也是难得的畅快了。
其实,当时农场职工的这种喝酒方法很普遍,干活回来喝的酒乃是解乏酒。春耕春播大忙、夏季麦收时节、“三秋”拾花季节,农场人个个忙得胳肢窝里恨不能再长出一只手来。这时候,回到家里忙里偷闲喝一杯小酒,也就是最幸福的日子了。
1967年4月下旬春播时,也是“文化大革命”正高潮时,抓革命、促生产的口号正喊得响。有一天,老天爷变了脸下起了雨,农场人趁机过起了“雨休”。照例,有喝酒爱好的职工趁着难得的休息日,千方百计地要精心准备几个下酒菜,邀上几个朋友喝一口,结果弄得连队烧酒房里存的两缸酒一下子卖完还不够。你想啊,这时侯不趁机喝点酒,再想痛痛快快喝酒,就要等到“五一”劳动节以后播完粮、棉,连队杀猪分肉庆祝的时候啦。那时,种子下了地,连队人人轻松,打一壶连队烧酒房烧制的高粱烧,职工小家杀个鸡、炒个蛋啥的,那下酒菜也是相当丰盛的,一般职工家庭的小饭桌都能摆上七八个像模像样的下酒菜。
开荒队有个老职工叫谯大牛,是个爱喝酒又很爽快的人。他家缺啥断啥从来就不断酒,而且老谯还有个习惯,从不一个人喝酒,总爱邀上仨俩邻居或者朋友一起喝。说起老谯家的下酒菜,几乎连队职工都知道:干炒出来的五香蚕豆,俗称“磨牙豆”,硬得用小锤子砸都费劲;咬不断嚼不烂的羊蹄子,上面没啥肉,啃起来满嘴咯吱咯吱响;还有不知从哪儿弄来的像皮条儿一样、己经发黑的牛肉干;韧而不软的鸡爪子;腌雪里蕻、咸萝卜……这些被不少人视为“没吃头”的东西,却在老谯家的酒桌上因“有嚼头”而颇受酒友欢迎。
傍晚收工后或是下雨天,老谯常常和几个投脾气的朋友凑在一起,嚼嚼豆子咸菜,喝喝农场连队自己生产的小酒,谈天说地,庄稼收成、时令节气,家长里短,老婆孩子……都是话题。这些“有嚼头”的东西只有配上“有嚼头”的话题,和着带有农场特色的烧酒,才能喝出嚼出耐人寻味的味道。
1969年,我下乡接受再教育到下五场工作,亲眼看见农场爱喝酒的职工们嚼着鸭头、鹅脖、鸡爪、羊蹄、猪尾巴、牛骨头……用这些皮包着骨头、骨头连着筋的东西当下酒菜,和很多不喝酒的人一样不理解。后来才知道,喝酒的人正是冲着这瘦而无肉的东西去的。看着这些农场汉子撕着、剔着、啃着、嚼着,满嘴里肉味,半天却没吃多少东西下肚,才理解这就是农场下酒菜的奥妙所在。
再后来,我参与其中,吃着、喝着、聊着,时间长了,才体验到这样喝酒才能喝得尽兴、聊得透彻,用这样的下酒菜就酒,直感觉喉咙处有一只小手不停地往肚子里拽菜拽酒,心眼里还想着吃饭时的大盘、蒸碗,喝酒的人就始终有念想、有盼头。
1970年9月,下五场一个叫王峰的老职工请我们几个下乡知青喝酒,酒桌上摆的主菜是油炸鱼——是他亲自到农场一个叫大滇魴的大水塘里捞的白条鱼,又配上当时流行的虾片、咸鸡蛋、油炸花生米、白菜萝卜、洋芋片等,再加上他杀了一只家养的土鸡,算是很丰盛了。俗话说,鸡吃骨头鱼吃刺。鸡骨头多自不必说,那鱼刺更多也是人所共知,不仅有主刺,而且还有横刺、细刺,而且鱼刺与鱼肉都是一个颜色,让人不好区分。但品酒吃鱼,有的是慢慢剔刺的功夫。油炸花生米,一次只能夹一粒,啃着鸡肉嚼着鸡骨头,都吃得花功夫、费时间,这正好放慢了喝酒的进度,给酒精的分解、挥发、排泄都留足了时间。况且,我们当时还不像真正的农场职工喝酒那样豪爽,喝酒吃菜的速度当然也极慢,主人几次提出要再加菜,都被我们拦住啦。
农场职工的下酒菜还与季节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,顺应着新疆北疆季节的变化。新疆的春天来得晚,到了“五一”节过后才有点菠菜、鲜韭菜,下酒菜就只有炒个鸡蛋、配些咸菜啥的。一到夏天,那新鲜蔬菜就多了,掐点荆芥、麻汁豆角、红焖茄子、凉拌黄瓜西红柿,秋季有刚挖的土豆、新收的萝卜白菜,冬天的白菜豆腐猪肉炖粉条,都可以摆上桌。韭菜要吃头茬的,豌豆角要吃麦收前的,扁豆角要吃打霜的,大白菜要吃下过霜后砍回的,味道才鲜美。这些道道,农场人心里都有数,所有的下酒菜都是绿色环保的,吃起来当然惬意顺心。
朋友老韩做下酒菜的手艺让我至今都记忆犹新。每每请我们几个要好的朋友一起喝酒,他家做的蒜泥黄瓜、麻汁菠菜、小葱拌豆腐、酸辣粉皮、糖醋白菜心……赤橙黄绿青白紫,别有一番风味。
1979年冬天,那时农场的日子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,我在家里请几个朋友喝酒时,虽然外边飘着小雪,但大家围着熊熊炉火,烫一壶热酒,品着卤煮的整只牛头当下酒菜,菜美心暖,就体验到只有在新疆农场才能享受到的独有的风味。再说,牛头肉既下酒又解酒,酒多人不醉,兴致自然高,何乐而不为?
那时,在农场喝酒,由于大家工资都不高,置办几个便宜的下酒菜,便当、绿色、天然、有滋有味,下酒、解酒、随心、助兴、实惠、科学。现在,在酒桌上和以前在农场工作过的朋友,说起那时的下酒菜,自己也编了几句顺口溜形容它:耐嚼有劲儿,少肉多味儿,耗时费事儿,应景四季儿,常冒凉气儿……
农场职工常说,喝酒不在意下酒菜有多好,但要有由头,要趁农闲时节,一起喝酒的人要对脾气心思。农场生活环境,追求平安和谐,几味农家菜摆上,几杯农场烧酒下肚,习习凉风,欲神欲仙,比起贪官、大款“一顿饭一头牛”心安自在多了。